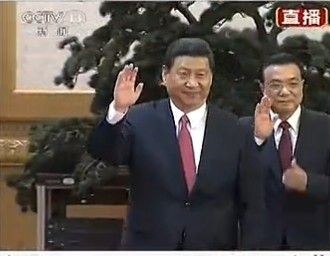柴静采访(资料图)
柴静采访(资料图)12月22日,广州遭遇冷空气剧烈降温,太古汇方所书店却即将沸腾。上千名读者挤在已经拉上铁闸的书店门口,要求进入,只为一睹央视记者柴静的真容。
柴静的新书签售活动原本没有安排广州站,“以为这里没人看中央电视台”。但这个夜晚,广州的这家书店却因为她的到来几近瘫痪,人群从门口蔓延至商厦的二、三层。活动结束后,书店的运营总监被带去派出所做笔录,并做出“不再举办类似活动”的承诺,否则将适用于“危害公共安全”的罪名。
虽然受到了读者近乎疯狂的追捧,可柴静并不认为他们和自己的关系,是偶像与粉丝。
“不是因为你,是因为你做的事”
如果不是出版新书《看见》,柴静并不清楚她的读者究竟是怎样一群人。
在冰天雪地的北京西单,站了四五个小时,有的拿着书看,有的在背单词,终于轮到自己签名时,对她往往只说一句话:“你辛苦了”。一名年轻的读者对她说:“排了这么长的队,我不是为了来见你,只是为了你做的事情”。柴静将这一幕写到了自己的博客里说,“嗯,知道”。
正是因为这十年来做的报道中的那些人,读者愿意对她有一点相知,这点对她来说,最重要。
这些年来,喜欢她的人越来越多,读者们在网络上建立柴静小组,把她的文字和节目收集起来。也有读者在谈论她的围巾、衣服、手提包,年轻女生在网络上写,“我也要戴条同样的红围巾去见她”,因为在《看见》的新书首发式上,柴静戴了一条暗红色围巾。甚至有自称是柴静粉丝的读者,曾在网络上造谣称“柴静被警察带走了”,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为她增加人气。
但作为公众人物,柴静从不透露自己的私生活,对于种种传言,她也几乎不回应。她说,读者并没有非要了解这些,“我看在我博客留言的读者,其实是没有这种愿望的”。
进央视是因为里边的人
十年前的柴静,20多岁,天不怕地不怕,不想在任何单位固定工作,不愿被坐班和办公桌束缚自己。她住在北京,给湖南卫视“新青年”栏目做节目,做一期拿一期稿酬,相当于自由撰稿人,没什么保障,但十分自由。柴静也根本没想过要去央视,如果不是陈虻给她打的那一通电话。
对于那时热爱自由的她来说,最终打破种种担忧的,是央视那年的年会。她在年会中看到了自由狂欢的劲儿,特别喜欢。新书首发式,崔永元、白岩松、张立宪等等好朋友的捧场,又让她找到类似年会的那种感觉。她喜欢和这样的人一起,是他们吸引了她进入央视。
刚进央视时,她总被陈虻骂。她不服气,对陈虻说,“我知道自己所能到达的度”。如今,回忆起当时的自己,她仍会不好意思地笑笑说,二十出头的人,对人生有种错觉,总认为人是向上攀登的,总觉得还有另一种在高处的生活,只要不断憧憬,总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,经了事儿之后,就落在了地上。
搞掂采访后发短信“赢了”
十年前的她做采访,总觉得这是天然赋予,“人民期待着我去问”。甚至她会在搞掂一个采访后,给编导发短信:“赢了”。而现在,采访不再是她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博弈,这项工作可能含有对人的冒犯,或者多少有些傲慢,“本来咱俩不认识,但今天坐下来,我就要来问你内心最隐秘的事情”。
她变得温和,更忠于内心的感受,她诚实地说和问,“如果我能承担,那我愿意和你一起”。
生活中的她也变得更为谦逊、谨慎,不轻易发表看法,避免草率地下结论。她对群像概念十分谨慎,不再会对广州这座城市给她的印象之类的大问题给出洋洋万言,但放在十年前,形容词和排比句或许早已脱口而出。在她眼中,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人,和具体的人接触所留下的印象,更何况,就连这个印象也在不断变化。
坐标系是事情,不是时间
2012年即将走到尽头。柴静没有年的概念,也很少去想这个时间点是否有特别之处,她的坐标系不是时间,而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。从2003年担任《新闻调查》出镜记者起,经历“两会观察”等等阶段,她至今已有了十年的央视经历。这个年底,柴静把个人成长心路与中国大事件糅合在一起写入新作《看见》。———从“调查”到“观察”再到“看见”,柴静说这是一步步地“后退”,一点点把视线放平,回归到事物本身。
十年前,央视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各条新闻的转载率,转载率高,第二天可以受到表扬,或者免受批评。或许是为了急于证明自己,那时的柴静总想做头条,而且也总能做到,因为有新闻资源。但慢慢地,她发现,如果有很强的目的性或者功利心在前,其实是做不好的。现在的她,很多时候是为了乐趣在做事,而不是为了成败,态度悠然。
看过她的节目和书之后,仍然有人质疑她过于容易自我感动,也有人质疑她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讲述得过于真善美。柴静说,想知道让人质疑自我感动的章节究竟是哪些,“或许那是不自知的”。但同时她也认为,书写完之后,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,只属于看它的人;而她,只是想诚实地写下自己的生命印象。
 长沙妹子获钢管舞冠军
长沙妹子获钢管舞冠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