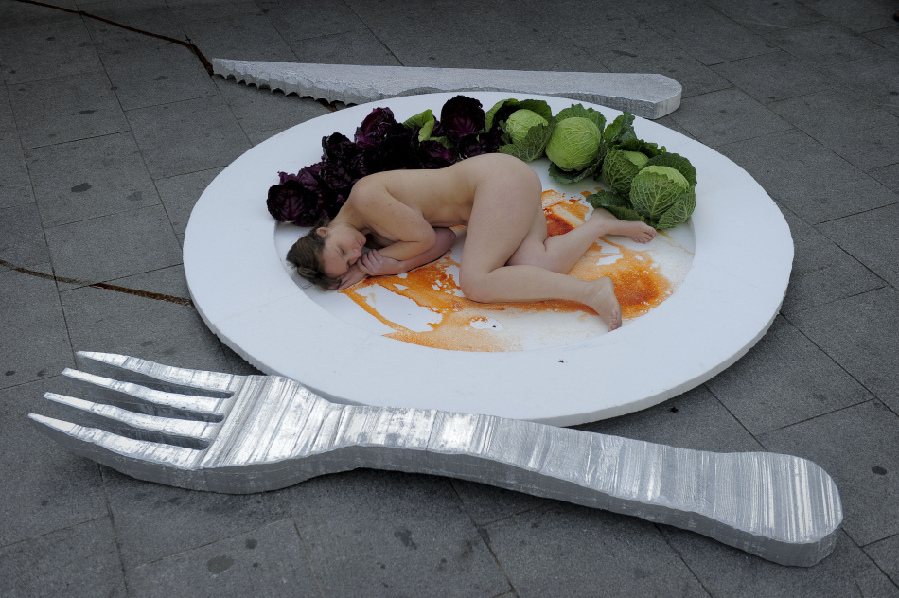《十三钗》录音师:让人听到打碎骨头的声音(2)
“那时,我、张艺谋、顾长卫站在桥头上听德沃夏克的《致新大陆》,那时候大家做电影很纯粹。”
记:人生中的很多第一次都是刻骨铭心的,您的第一部作品《孩子王》对您来说印象是最深刻的吧?
陶:是,那时很纯粹,为了一种感受,我、张艺谋、顾长卫站在桥头上听德沃夏克的《致新大陆》,我们一晚上都在找感觉,现在根本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。那时候大家做电影很纯粹,现在碰到顾长卫,我们经常感慨,永远不会有那个时候了。
记:当年大家对电影的概念都还比较模糊的,更不用说音效这种专业学科了,您怎么会把它当成今后一生的职业?您当时就看到自己的未来吗?
陶:那时候是不由自主,没有任何选择权。我那时被分配到农场务农,后来有了考电影学院的机会。两方面使我成为录音系的一员,我理工科不错,另外 我会拉琴,录音系正好是这两项的结合。本来前几天还在挖沟呢,没过几天就可以进电影学院,就不由自主去了。做了以后,开始感受到声音的魅力。我觉得感受最 重要,并不是我的耳朵多灵敏,物理多好,还是对声音创意的感受,其实是用脑用心的事。
记:在您的创作生涯中,哪部电影或者是哪次经历对你影响特别大?
陶:很难说。有的电影花钱很少,比如《有话好好说》《山楂树之恋》。有的是大投资,包括《霸王别姬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。但不管电影投资大小,对一个做声音的人来说,他的感受是一样的,就是说,一个朴实的女人和一个妖艳的女人,只要是你真喜欢的话,感受是一样的。
记:一部电影,音效到底占有怎样的位置?
陶:小时候看电影,因为影院效果差,画面还在放,声音突然没有了,底下就有人鼓倒掌,于是机器停下来重放这一段。所以,观影时声音是必不可少的因素。如果声音做不好,会把画面做得乌突突的,声音做的好,就像空气流动,让画面更绚丽,更有纵深感,更有质感。
记:您在生活中是怎样捕捉这些声音的,您会时刻留意身边的一动一静吗?
陶:我认为最主要是要了解生活,不在于又出了什么新CD,又发明什么新设备了。其实杜比7.1环绕声给创作上带来了可能性,这一点毫无疑问。做电影技术方面的人最聪明、有效的办法,是让你的创造力提高,这种技术我愿意接受。
“为了抢克里斯蒂安·贝尔的档期,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妥协。”
记:您说过,作为电影的声音创作者,不能太彰显个人的个性喜好,坚持或者放弃,都不如妥协来得更智慧?但是妥协会不会丢失自我?
陶:就像两人签合同,我有幸每次签的都是好合同,不是那种烂合同。在电影当中要和对方有一些妥协,比如我人力多,我就可以降低一些人工的标准。当然有些是必须坚持的,比如质量,妥协带来的另外一个词就是坚持,不能一味妥协。
记:具体到《金陵十三钗》,有没有进退两难、必须妥协的情形?
陶:有,大量的。很挣扎又充满挑战。比如要抢克里斯蒂安·贝尔的档期,拍大全景时,现场八台机器对准他,但话筒杆不可能接近演员,录不到他的台词,这个时候就要妥协,否则档期一到,人都走了,还拍什么?那时候我只有放弃,用其他方式来弥补,这时候就要看你的能力了。
记:包括《功夫之王》,是您第一次与好莱坞合作,东西方文化差异如何平衡?
陶:我是上海人,我很务实,跟老美合作,投资方是老美,关键人物都是老美,有些地方就必须妥协。你要知晓他们的习惯,比如《功夫之王》里金箍棒 的声音,他们对高频的金属声特别反感。对中国人来说,《急急风》都可以听得津津有味,更别说这种声音了,中国人听了会很兴奋。但美国人不要,所以我就变成 了低声的金箍棒的声音。这些都需要创意。
记:和陈凯歌、张艺谋的合作中有没有这样的冲突?
陶:这种冲突是有的。一个人的想法跟另外一个人肯定是不一样的,你要让一部作品尽量靠近一个人的想法,他傻也就是傻到底,好也就好到底,在他那 个好的方式上好到底,这是聪明的做法,所以尽量多听他的,多揣摩他的。你的创意要在他的体系当中体现,你看一个电影就会感觉特别的规整,特别像一个人。
分享到:
相关报道
热点新闻
- 1. 李湘回应与谢娜抢台词争一姐:我们关系很好(图)
- 2. 宁财神给周迅写情书引发热议:再不表白就晚了
- 3. 杨钰莹将来长录制芒果春晚 经纪人否认复出受阻
- 4. 张柏芝含泪献唱谢歌迷 男粉丝大喊愿帮其养小孩
- 5. 王菲确认上央视春晚 与陈奕迅合唱《因为爱情》
- 6. 赵忠祥被指利用节目卖古董 受访回应“炫富说”
- 7. 刘德华证实朱丽倩已怀胎四月 留港拍戏陪妻待产
- 8. 王力宏舒淇被曝蜜游度圣诞 隐瞒王母继续地下恋
- 9. 拍床戏累得连滚带爬的10大明星(图)
- 10. 张柏芝为复合摆桃花阵 儿子成软化谢霆锋关键

 长沙平头男南京持枪抢劫
长沙平头男南京持枪抢劫 快递员为抓偷车贼身中5刀
快递员为抓偷车贼身中5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