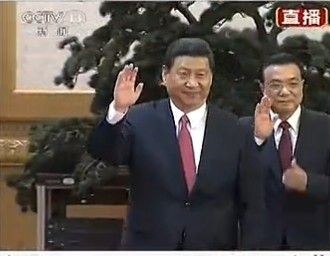火车来之前大约五分钟,道口蓝紫色的灯会变成红色,铁路工人挥舞小红旗禁止车辆与行人通过,长长的栏杆缓慢放下——这几乎是我童年百看不厌的场景。当然有时候火车也会迟到,等待火车进站的间隙当中,往南边看,是一排排和我家一样的平房,往北边看,有高高的绿色的龙门吊。舅舅说,长沙东站是一个典型的官督商办集资建成的老站,之所以选址在小吴门到伍家岭一带,是因为这里处于水陆交会的地方,便于车船衔接。我已经不上铁路幼儿园了,外婆在家里教的东西比幼儿园多很多,所以他说的东西虽然有点深奥,连蒙带猜也能明白个七八成。我对舅舅说,我一生出来,火车站就老了。踌躇满志的大学生舅舅不知道,将来这个外甥女会被火车带到无数个连他都没有去过的地方。
那时候五一路上的车辆很少,大多是公交和自行车。人们好像一点都不赶时间,也许大家和我一样,觉得能看到火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他们在公交车上聊天打招呼,低头拨弄车把上挂的青菜,和我一起等待火车的汽笛声铺天盖地而来,淹没尘世间一切声音。
终于有一天,某台公交车抛锚在铁轨上,酿成了火车撞汽车的惨剧,各方消息显示出长沙的交通日益繁华,必须把铁路移出城区。
上小学那年外公家面临拆迁,老邻居们有的住到向韶村,有的去了阿弥岭,有的搬往朝阳路,都是铁路职工居民区,对老人们来说住进楼房真是很隆重和值得庆祝的事情,爸爸和舅舅们放了鞭炮杀了鸡,所有的细软都被装上大卡车。清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张旧照片,是个很帅的年轻人,穿着宽襟削肩的制服,每一颗扣子上都有铁路标志,妈妈说那是年轻时正在修建粤汉铁路的外公。
离开了热闹的大家庭开始是不太习惯的,我曾经偷偷坐上11路车回外公的旧房子,埋在泡桐树下的七个玻璃球不见了,外婆种的兰花不见了,以前门口放水缸的地方只留下一个圆圆的白印子。再后来,发生悲剧的铁路道口也不见了,道轨拆除后辟出一条名叫芙蓉路的新马路,这里也由东区更名为芙蓉区。
尽管路过的机会不多,我还是喜欢仔细辨识一切与过去相关的鸿爪雪泥:曾有火车经过的八一桥菜场变成了银行宿舍,小吴门邮局不知道什么时候聚集了一群刻章的人,小时候玩泥巴的苗圃变成家乐福超市。老火车站日渐面目全非,我也没有像家人预计的那样成为铁路职工,而是念了中文系,去监理公司写合同。

 长沙妹子获钢管舞冠军
长沙妹子获钢管舞冠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