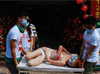“我不怪任何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。”张爱兰说,“我只想我妈妈。她在住院,气哭了。”
但是,妈妈没有来看她。“她接我电话说,要我回去跟她一起死了算了。”
张爱兰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。“出事”后,妹妹从北京赶回益阳老家照顾母亲,张爱兰打电话回去,妹妹对她说,不要再联络了。
她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独者。
“心愿未了,让您担忧牵挂的。我最疼爱妈妈”
得不到母亲的包容,张爱兰说,这让她最伤心。
她的空间里,今年1月份的一篇日志标题是:“心愿未了,让您担忧牵挂的。我最疼爱妈妈”。打开日志,里面只有三个字和一个标点符号:“20年前,”这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。
20年前,她10岁,生活在益阳安化的小山村里。
小学三年级课堂上,她用针和墨水在手腕处刺了一个“爱”字,回来被哥哥一顿骂,后来,用水洗,用刀片刮,盆子里的水都有血丝了,字却怎么也洗不干净。现在,这个“爱”字还是醒目地长在她的手腕上。
“爸爸在我5岁时就过世了。我唯一的记忆是,那时,我会坐在他高高的肩膀上去看戏。”
张爱兰说,看完戏回来,她会学着唱,“都是黄梅戏,很悲的那种调子。爸妈都觉得奇怪,我怎么对唱戏那么有天分。”
她说,父母的话,在自己17岁那年得到了验证,高中放暑假,她随姨妈来到涟源,路过一个歌舞厅,她停住了,央求姨妈借50元给她去唱歌。她唱了一首《烛光里的妈妈》,赢得满堂喝彩,歌舞厅老板让她做暑期工兼职唱歌。
这是她“驻唱歌手”生涯的开始。
她干脆不上学了。她说,当时自己跟母亲说,希望去外面唱歌,闯出一番名堂。母亲跟她讲道理,说外面的钱不好挣,特别是姑娘家,应该读点书,再找个好人家。她不听,跟母亲说:“我就是为了唱歌而活的。”
最终,母亲没有拗过她,叮嘱她要听话,“要与家里联系,挣没挣到钱都要经常回来”。
张爱兰说,自己的决心是:一定会成功,没有成功决不回来。
她离家时不到18岁。当时,她去理发店里剪了个流行发型,拎着两个行李箱就出了门,来到涟源。
听到手机里的《你在他乡还好吗》,泪流满面
张爱兰渐渐成了涟源当地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。
两年后,2001年,她从涟源来到长沙——在这个歌厅文化红极一时的城市,铺开了自己的“野心”。
又是两年过去。她在伍家岭开了一家小歌厅,生意不错。由于和哥哥关系不怎么好,开歌厅之后,只回过一趟老家,“晚上,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,半夜醒来,发现妈妈在抚摸我的脸,我不知道她怎么了,也没有问,继续装睡。”
她在长沙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溃败。
她说,一个家在星沙的男人经常来她店里唱歌,后来,两人谈起了恋爱,她觉得,那个男人在一些生活细节上都表现得很爱她。
“去年7月,他对我说,有朋友愿意帮忙一起把店面扩大,需要一起投资。我也没有怀疑,把26万元存款全部取出来了,装在手提包里。第二天一醒来,发现他不见了,我的钱也不见了。再去店里,发现店子也被转出去了。”张爱兰说,自己跳过两次江,被人救起了。
伤心了两个月,在朋友帮助下,她决定重新回到舞台,去了株洲一家比较有名的歌舞厅。
她说,应聘的时候是下午,歌厅里没几个人,老板让她试唱一首拿手的曲子。
“我唱了首光头李进的《你在他乡还好吗》。这不是我最拿手的,但是,我当时特别想唱这首歌,因为没有人唱给我听,那我就自己唱给自己听。”
这首歌,张爱兰用手机录下来,现在还存着。
她对记者说:“想听吗?我放给你听。”
很明显,这首歌她唱得太过用力,每一句歌词的尾音都被她有意地拉长抖了一下。
“你在他乡还好吗,是否想过靠着我的双肩,你那不再熟悉的笑容,对我可是一种敷衍……”歌声从手机劣质音响中传出,张爱兰已是泪流满面。
朋友不愿透露姓名:不想别人知道我跟她有过来往
在这家歌舞厅,张爱兰认识了一名王姓男子,即现在小孩的父亲。
她说,对方是东北人,人长得不错,对她也很好,他们很快就在一起了,后来,她怀孕了,问对方要还是不要,毕竟两人没结婚,“他说当然要,马上就结婚”。
她说,几天后,对方跟她说,要回老家请示父母,还要筹钱来株洲结婚,她很开心,送他上了火车。
“后悔了。我都没认真看火车票上的目的地,只记得发车时间是晚上7点10分。”张爱兰说,第二天,对方手机就关机,后来成了空号,“我那时还以为,他是遇到了阻力,我相信他会说服家人接受我的。”
现在看来,她失望了。
而后,张爱兰离开株洲,又回到了长沙伍家岭。
今年春节,她在一家宾馆度过,她说,受了太多波折,自己不愿出门,怕见人,“好像得了抑郁症”。
孩子大概5个月时,她感觉自己除了怀孕的正常反应外,身体还有些其他异样,不确定是不是性病。她没敢去医院检查,甚至还抱着一丝侥幸,直到孩子出生。
医生检查,她身患多种妇科疾病,血清试验为梅毒阳性。随后,她接受了媒体采访。面对镜头时,她没有捂住脸,只是小心地拿被子挡了下巴。“除了下巴,我没有不愿意暴露在公众视线里的东西。”
张爱兰的下巴有一块疤痕。她说,那是读高中时初恋男友不小心用开水烫伤的,那是自己“唯一自卑的需要遮盖的地方”。
新闻播出两小时后,母亲来电话了。张爱兰说,自己那时才意识到,大事不妙。
当时,她没有医药费,打电话给几个朋友,朋友有的把她数落了一顿,有的干脆说,打错了。
现在,她也不愿给家人打电话,她说,不想妈妈再伤心,哥哥妹妹也和她断绝关系,不想打扰他们。
记者找到张爱兰一个以前的朋友。他不愿透露真名:“不想别人知道我跟她有过来往……”
这并不让张爱兰意外,她现在也无暇顾及这些,“孩子的下一罐奶粉钱还不知道在哪里。”
8月30日,她去一家招服务员的餐馆应聘,遭到老板的拒绝。这个老板认识她,并且看了新闻,跟麻将馆老板娘一样,他“不能吓跑顾客”。
继续驻场唱歌?张爱兰说,目前身体不允许,而且长沙很多歌厅老板和朋友,都已对她避而远之。
她已然被孤立。未来何去何从,希望在哪里?答案,似乎也不在她自己手中。
[记者手记]释放我们最大的良善
张爱兰说,她之所以接受采访,是希望女儿将来能够看到报道。
“我爱我的女儿,不会做傻事。我只剩下女儿了,我会好好把她抚养大。我希望女儿将来相信,妈妈也是受害者。”
其实,人的一生,很多时候可以看成是一段段“搜索”的历程:搜寻、追逐自己的可能与梦想。这段旅程,难免会迷失在一个个岔道口,颓废,甚至堕落。而在当前这个信息传播的社会平台中,人们又常常成为被“搜索”的目标。
而张爱兰,因为媒体的报道,在社会的偏见中,留下一个落寞而孤独的投影。
对这名女子,你又会怎样?是避而远之,是毫无医学常识地将她打牌的板凳扔掉?还是提供物质捐助,稍表你的同情?
要知道,任何物质资助,都显得表面而肤浅,更关键的,是我们内心和整个社会的反思:怎样释放我们最大的良善,让张爱兰们不再落寞,不再孤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