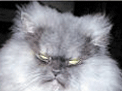去南方最好在春节前,很多人都会把不要的衣服丢掉。那我们还要挑着穿,选好一点的(眯着眼睛,抬着头看远方,干咳了一声)。因为过年嘛!——老李,辽宁人,一头长发
这是一群无家可归的人。
他们来自天南海北。华灯初上时,他们不约而同汇集在一起,沿着墙脚席地而睡。
他们经常蜷缩在车站、地下通道及有可能挡住雨水、阳光和夜露的地方憩息;他们要脸面,讲尊严,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接受施舍;他们说不偷不抢,身上每一样东西都是弯腰捡来的。
在多数人的眼里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:流浪汉,或拾荒者。而他们则称自己是“候鸟”,天再冷些,就会离开这座城市继续往南走。本版撰文/记者吴和健
隔段时间会花几块钱去澡堂洗澡、洗衣
10月16日晚8点,风起。
芙蓉广场立交桥下的东面和北面,有十几个铺盖沿墙脚摆开,有被子的抱着被子裹成一团,没被子的就缩在一个大编织袋里,有的还只有一张不能遮挡身体的草席。黑夜里,他们像虫茧一样粘在墙脚。
71岁的老林戴着一顶帽子坐在铺位上抽烟。两床单薄的被单,一床垫在草席上,一床折放在一角。“现在盖着有点冷了。”老林是这里的“老住户”了,他的铺位比其他人的铺位要整洁许多。他说自己是邵阳人,上世纪70年代招工到了长沙鼓风机厂,会刨、铣、冲、镗等各项技术,也会看图纸加工,后来下海经商破产,老婆离婚带着儿子走了,之后杳无音讯。“再也没能翻过身来。开始还能帮别人打工,后来年纪大了,眼睛也不好,就捡点破烂。原来住在火车站,前两年才搬到这里。”老林从口袋里掏出两团棉花,往耳朵里一塞,“这样汽车的声音就不会那么吵了。”
“衣服有的是捡的,有的是别人送的。”老林说,捡矿泉水瓶子卖的钱还不够吃饭,身体有毛病也只能撑着。不过,每隔那么一段时间,他还是会花几块钱去澡堂洗澡、洗衣服,“去饭馆或垃圾桶里捡饭也不会让人很讨嫌”。
“从来没偷没抢,就是原来破产也没有欠过别人的钱。”这是让老林聊以自慰的。
如果再冷点,就要再往南走了
老林的“邻居们”来自辽宁、甘肃、福建、湖北等地,除了几个年纪大的,老林说他们基本上来了又会走,走了又再来。来去间带着不同的故事,也带着难以言说的秘密。
老陈,山东人,长一脸络腮胡。记者见到他时,他正夹着一本厚厚的《毛泽东选集》,靠着地下通道的一个柱子,坐在路旁吃饭。“都是捡来的。”老陈指着地上的一个饭盒和两个饮料瓶边吃边说,一辆小车喧嚣着从他身旁开过。
“出来十几年了。”老陈不愿透露外出的原因,反倒问了记者一句:“如果你住在家里,去楼道或外面捡破烂,邻居或熟人会怎么说?”老陈戴着近视眼镜,穿着旧雨衣雨裤,只是脚下穿着一双凉拖鞋。“冷是冷点,但衣服捡了不少。”老陈掀开雨衣,里面还有一件旧毛线背心。他说如果再冷点,他就要去更南的地方了。“我们就是‘候鸟’,等天气暖和了又往北走。”
老李,辽宁人,一头长发,在这些人中显得很突兀。“2005年去的拉萨,先去的西宁,再走到了格尔木,最后坐汽车去的拉萨。”老李说十几年前,家里没有了一个亲人,他就开始在全国漂泊,包括西藏。
老李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账。“如果回去,要吃饭吧。”老李说,就算领了低保,那房租一个月也要几百块钱,还是不够吃饭。“如果死了,要花钱吧。”老李说,就是买块墓地他现在买不起。
说起找工作,一旁的老林摇了摇头,指着蒙头大睡的一名老人说:“他是名厨师,有全套雕花工具,后来被偷了,买不起。”停顿了一下,又补充说:“都嫌他老了!”
去南方最好春节前去,会有好衣服捡
“白天捡瓶子卖钱,晚上再回来。”老陈说,少的时候一天只卖几块钱,多的时候也就十几二十块钱,“都一样,都要捡饭吃。”
“我捡的饭比他们买的饭还要好。”老李说捡饭也有学问,就算别人花八块钱去买个盒饭,也不一定有他捡来的饭菜好看。但诀窍在哪?他又不愿多说。
就捡饭这事,老李还说了个故事:2008年,他在深圳遇到不少穿着名牌、身无分文的人与他一起挤在天桥下,饿得发慌也不知道捡饭吃,他看得出他们是不好意思。老李说那段时间他接济过不少这样的人,“接过我捡的饭扒拉几口就吃完了”。说起在南方的日子,他说春节前去最好,很多人都会把不要的衣服丢掉。“那我们还要挑着穿,选好一点的。”老李眯着眼睛,抬着头看远方,干咳了一声说“过年嘛”。
地下通道里,他们演绎着各自的快乐与悲伤。老陈就对前段时间被赶走一事耿耿于怀。“我们什么事也没干,抓了我们就走。”他说前段时间来了一批人,将他们的东西弃之路边,还把人带走后,招待了几天又给放了出来,而他们原来的东西却统统不见了。“我们身上的每一件衣服,每一个瓶子,都是我们弯腰捡的。”老陈说。
在记者为老陈拍照时,睡在他身旁的两个年轻一点的“候鸟”突然起身并企图动手打人。老陈下意识阻止,转过脸后,说了两个字:“素质”。